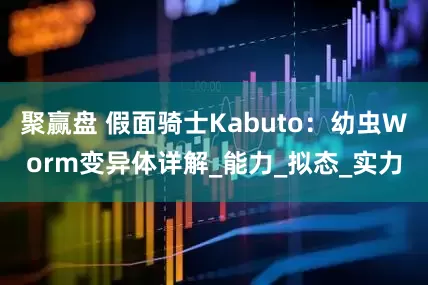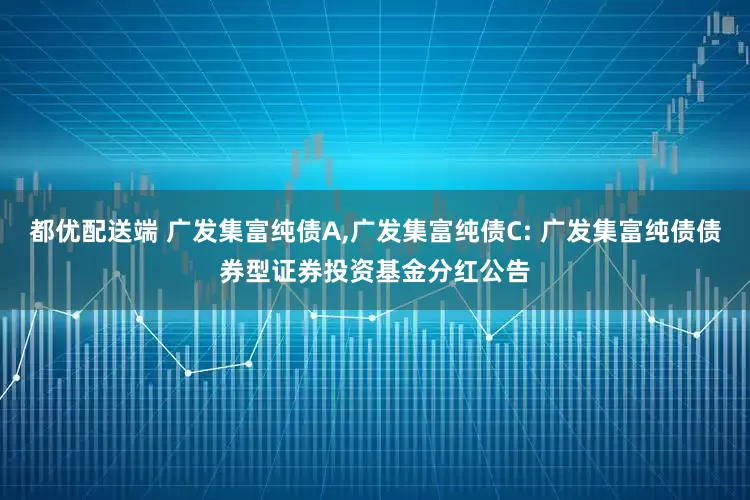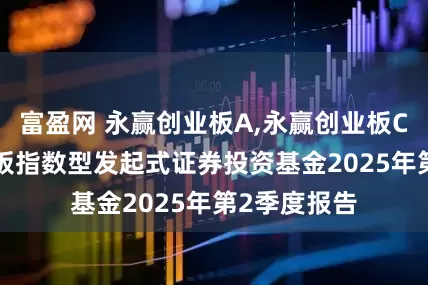北大教授评价电影《戏台》 三层戏台映射时代变迁!陈佩斯导演的电影《戏台》改编自他备受赞誉的同名话剧。从舞台到银幕,这不仅是媒介的跨越,也是文化表达的扩展。电影通过“戏台”的隐喻,将剧场中的故事推向了社会百盛证券,嵌入当代文化讨论的核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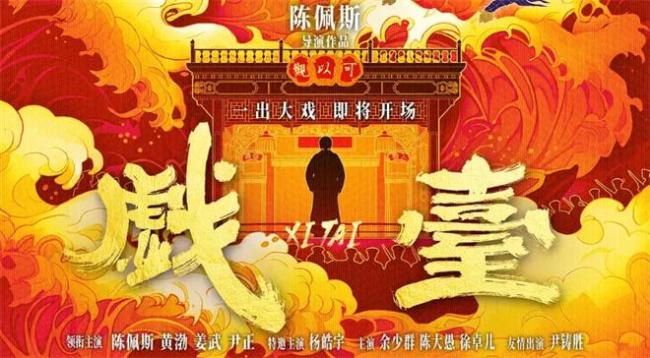
电影开篇展示了北京城外雪地里的一场攻防激战,预示着京城即将易主。一列火车驶入,交战双方暂时避让,随后继续厮杀。这一荒诞场景为全片奠定了基调:在“戏中戏”的结构中,权力更迭的混乱与艺术生存的困境交织成一幅民国浮世绘。

电影呈现了三重戏台。第一重戏台是北京城,城墙下的炮火、洪大帅进城的喧哗以及街头的市井闲谈构成流动的“社会戏台”。鲁迅笔下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描述在此具象化,政权更迭如戏服更换,百姓则是被迫的看客与配角。

第二重戏台是影片的主要场所——德祥大戏院。电影使用前门外景和湖广会馆内景百盛证券,再现了一个典型的民国时期北平老戏园。围绕名角金啸天的演出,戏院内外上演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又滑稽异常的事件。从三天戏票售罄到南城一霸刘八爷的到来,再到洪大帅的包场,戏园成为各方势力汇聚的地方。金啸天因吸食鸦片晕倒,送包子的伙计“大嗓儿”被洪大帅钦点为霸王,一场闹剧由此展开。

第三重戏台是真正的老戏台。即将上演的五庆班“打炮戏”里的大轴是《霸王别姬》,这部由梅兰芳创编的经典京剧作品,在影片中也承载了丰富的象征意义。《霸王别姬》的创作背景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变迁。电影中,洪大帅代表权力,由于他对京剧的无知,出现了以送包子的伙计“大嗓儿”饰演霸王的笑剧,以及强令修改《霸王别姬》结尾的闹剧。戏班班主侯喜亭则委曲求全,体现了乱世下艺术的卑微与扭曲。

在这方小戏台上,两个霸王和两个虞姬的故事交织展开,展现了艺术在强权挤压下的分裂。真艺术(金啸天)沉溺于鸦片,假艺术(大嗓儿)荒诞登台。大小戏台一层套着一层,喜剧包袱层层剥开,《霸王别姬》的情节与设定成为影片的核心。

这种以“戏”为核心的戏剧性结构,给演员们提供了广阔的表演空间。姜武扮演的洪大帅野蛮而天真,陈佩斯扮演的戏班班主侯喜亭世故而老到,杨皓宇扮演的戏院经理趋利势利,尹铸胜扮演的刘八爷土豪排场,陈大愚扮演的教化科长谄媚变色,黄渤扮演的“大嗓儿”痴迷笨拙,尹正扮演的金啸天迷失睥睨,余少群扮演的凤小桐柔中带刚,每个角色都得以充分展示。

这些“表演”的前提是贯穿全剧的“戏”。“戏”或戏剧性贯穿戏曲、话剧与电影三种媒介,建立起假定性与想象力的统一。陈佩斯以夸张的表演解构严肃命题,揭示“表演性”如何贯穿中国文化——人生如戏,戏台永不落幕。

电影开头的北京城让人联想到郭宝昌导演的《春闺梦》。在郭宝昌的作品中,戏台随时代变迁,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历史。陈佩斯的《戏台》同样构建了一个“戏台”上的中国,这是一个观看中国的窗口,也是一个可剖析的微缩模型。陈佩斯一边展现形形色色的人物,制作纷纭万端的民国社会万象,一边剖析其中的情感与人性,并表达自身的艺术理念。

陈佩斯探讨的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核心命题,即鲁迅式的中国国民性的解析。在喜剧背后,他表达的是那一代人的理想所在,即艺术何为?陈佩斯试图召回这些问题与经验,一只手如戏班一般抵抗绝望,另一只手则以戏剧与电影记录这个时代。电影《戏台》因此成为照见历史与当下的一面镜子。
 百盛证券
百盛证券
淘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